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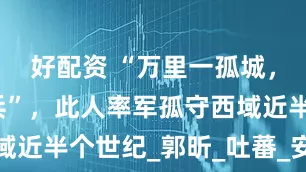
前言:一提到唐朝,很多人心中都会涌现出满满的好感。自建国以来,唐朝在经济、军事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,因此被后人冠以诸多光辉的称号,如“开放”、“自信”和“盛世”。当年,不少邻国都为强大的大唐所折服。波斯王卑路斯甘愿远赴洛阳,出任大唐的右威卫将军;于阗王尉迟胜在得知安史之乱爆发后,毅然将王位传给弟弟,自己率军奔赴中原,助力平叛。
连唐僧这位普通僧人,在西天取经途中,遇见谁都自信地说道:“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。”凭借这句话,他立刻赢得了各地城邦国主的尊敬,甚至亲自出面接待他。这样气势磅礴、底蕴深厚的大唐,并非凭运气,而是依靠一代代忠义之士在对外征战中铸就了无数传奇,比如孤守西域近半个世纪的郭昕,他用铁血行动诠释了大唐的忠诚与刚强。
1、受命于危难之间
7世纪的雪域高原上,多个政权林立。经过长期兼并和战争,弱小国家逐渐被淘汰,最终形成以吐蕃、羊同和苏毗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不久,松赞干布继承吐蕃赞普之位,他平定内乱,灭亡羊同,将首都迁至逻些(今拉萨),逐步建立了欣欣向荣的吐蕃王朝。俗话说“一山不容二虎”,吐蕃与唐朝难以和睦相处。吐蕃的西面和南面有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,北面是昆仑山脉,唯独东面地形开阔,成为两者争夺的焦点。
展开剩余84%从唐太宗时期的“和亲”,唐高宗时期的“大非川之战”,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,到唐中宗时期的“和亲”,再到唐玄宗时期西域和河西堡垒的攻防,吐蕃与大唐在这些地区纠缠百余年,总体上大唐占据优势。但安史之乱爆发后,唐廷从西域和河西大量抽调兵力应对内乱,吐蕃趁机进攻,甚至一度攻入长安。虽然后来唐代宗倚仗郭子仪等名将将吐蕃逐出关中,但河西大部分土地已落入吐蕃之手。
河西地处西域与关中之间的咽喉,一旦失守,西域就成了孤岛。郭子仪建议唐代宗选派得力干将巡抚河西、安西等地,以稳固防线,削弱吐蕃对关中的威胁。时任左武卫大将军的郭昕(郭子仪之侄)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一重任。他途经河西走廊,抵达安西都护府,途中所见既让他感动又令他忧心忡忡——感动于河西节度使周鼎、北庭都护曹令忠(赐名李元忠)等将士坚守边疆的忠诚;忧虑于吐蕃攻势日益猛烈,朝廷难以给予援助,这样的坚守还能持续多久?郭昕抵达安西后,被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留后,肩负起维稳安西都护府的重任。
然而,真正先失守的却是河西,肃州、瓜州、沙州、甘州相继被吐蕃攻占,西域顿成唐朝的“飞地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除安西都护府外,北庭都护府也负责天山以北地区的防务。
2、孤悬西域
吐蕃得势后毫不手软,持续蚕食西域。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既得不到朝廷兵力支援,也难以获得物资补给。身陷绝境,郭昕带领将士开展屯田自给自足。为了促进西域经济发展及商品流通,他甚至组织铸造货币。考古发现,在阿克苏等地出土大量“大历元宝”和“建中通宝”,均为当时大唐军士在西域铸造。
公元781年,郭昕等派遣使者通过回纥借道,辗转万难回到长安。此时郭昕已在西域坚守十五年。唐德宗得知西域仍属大唐疆土,喜出望外,立即加封郭昕为安西大都护,赐予武威郡王爵位,且对随从将士给予厚赏,不少人甚至越级七等授官。尽管如此,郭昕他们更需要的却是实际的军粮和兵力支援,可惜唐德宗无力满足。
不仅没有援助,唐德宗甚至萌生与吐蕃议和的念头。相比唐代宗对国土坚决捍卫,唐德宗在泾原兵变及长安失守时,竟有意借吐蕃之力平乱,甚至不惜割地求和,实质上是把郭昕等忠义将士“卖”给吐蕃。
幸亏名臣李泌及时反对,他认为安西和北庭士兵本就孤立无援,长期自力更生守护边疆,这份忠义感天地,若将其交予吐蕃,无异于背叛忠诚,未来谁还愿为国效忠?李泌历经玄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朝,声望极高,他的反对使唐德宗不得不打消议和念头。泾原兵变也未酿成大祸,很快被名将李晟等人平定。
3、安西与北庭互为犄角之势
朝廷不可靠,郭昕只能自寻盟友。他积极联络回纥、沙陀等部落,与他们共同抗击吐蕃,毕竟他们同受吐蕃威胁,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”。但随着吐蕃日益强盛,回纥觉得与唐军联手代价过大,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,双方配合日渐松散。
当外援失效时,郭昕依然有自己的帮手,北庭都护府即是其重要支撑。郭昕到来前,北庭都护李元忠便与吐蕃展开了持久攻防。郭昕抵达后,李元忠给予了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,协助他屯田生产,完善两地驿传体系,使安西和北庭形成南北呼应的防御态势,“扼吐蕃之背以护萧关”。吐蕃因北路受阻,转而向南进攻,给郭昕一线缓冲。值得一提的是,郭昕被封郡王时,李元忠也获封宁塞郡王。
公元784年,李元忠病逝,由忠义之士杨袭古接替。公元790年,吐蕃联手葛逻禄和白眼突厥围攻北庭。原本葛逻禄与白眼突厥均亲唐,问题源于回纥不讲义气,总欺负他们,且大唐难以调停,导致两部族投靠吐蕃。葛逻禄尤为叛逆,早年高仙芝在恒罗斯之战败绩,即因其背叛。
单靠吐蕃,唐军尚难抵挡,如今再加葛逻禄和白眼突厥,杨袭古与郭昕的协同力量难以发挥。形势危急下,杨袭古与回纥联手抗敌,兵力仍悬殊,最终只能带着两千余残兵退守西州。回纥见形势不妙,欺骗杨袭古等人至大营,将其全部斩杀,昔日安西的坚实后盾北庭宣告失陷。
4、独木苦撑十八载
北庭失守后,吐蕃集中兵力猛攻安西。郭昕等安西将士再次失联,令人震惊的是,他们竟在险恶环境中坚守了近二十年。据考证,郭昕可能在公元808年吐蕃攻破龟兹时阵亡,当时唐朝已是唐宪宗执政。著名诗人元稹的《缚戎人》讲述了一名从吐蕃军中成功脱逃的安西老兵故事。
老兵家乡位于长城脚下,少年随父戍边安西,多年与吐蕃鏖战。“自言家本长城窟,少年随父戍安西”正是写照。其回忆中,元和三年冬夜,吐蕃军突袭,四周无地可依,“阴森神庙未敢依,脆薄河冰安可越”。此“阴森神庙”与“脆薄河”分别指今日库车县西南的库木吐喇千佛洞和发源于天山的渭干河。
安史之乱后,西域唐军难以补充,许多士兵在此成家,父子相继守边。很多人从少年戍守至暮年,尽管白发苍苍,依旧拿起武器,怀揣“忠义”之心,誓死报国。“近年如此思汉者,半为老病半埋骨”道出他们的无奈与坚守。面对生死抉择,他们选择了忠义而非苟且求生。
那些眼神如鹰隼般锐利坚定,那些残破却依旧飘扬的大唐军旗,郭昕等人的明光铠已失光泽,手中陌刀百战成痕。号角声中,吐蕃军浪潮般扑向龟兹城,唐军用尽弓箭、石块、木头顽强抵抗,以生命捍卫大唐军人的尊严,铸就不朽传奇。四十二年如一日,他们无愧于心,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。
倘若郭子仪知晓侄子最终结局,恐怕不会悔恨。他本身忠义无双,征战数十载,亲人多有战死,绝不会因侄子牺牲而放弃西域防守。反倒会为侄子尽忠报国而感到自豪,郭氏家族自有骨气,绝不容软弱。
有人质疑,昔日大唐已不复往昔辉煌,内忧外患频仍,西域这块“飞地”岂非鸡肋?郭昕守护几乎注定失守之地有何意义?其实,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豪情,并非简单的“应不应该”能够解释,那是大唐的荣耀。向郭昕致敬,向所有忠义之士致敬,向所有孤勇者致敬。
参考文献:
《新唐书》
《唐实录》
《资治通鉴》
《西域研究》
发布于:天津市盛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